方如良
细细想来,我对三界一直抱有复杂的情感。
幕阜山脉沿湘鄂赣边界绵延千里,在三界给通山留下了最原始、最广袤、最茂密的一片丛林。曾经的三界,喧闹过,富足过,辉煌过,也冷寂过,贫困过,落寞过;一段时间它是人们聚焦的中心,另一段时间又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,就像一个多面人将许多矛盾的情感糅于一身,它真实的面孔,让人一时难以厘清。
(一)
最初,我对三界的印象不够好。
大学毕业后,我工作的第一站在厦铺中学。三界当时是个小乡,隶属厦铺片区。深秋的一个周末,我去三界中学看望同学。破旧的客车一路上哼哼哧哧,像哮喘病人一样走走停停,两旁的草丛布满了厚厚一层灰垢,病恹恹的,没有一丝生机。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颠簸,穿过重重山峦。沿途岔路口,不断有旅客下车,转眼间就消失在山山坳坳的密林深处。直到暮蔼沉沉,车子停在一处谷地,四周堵满了黑黝黝的高山,三界终于到了。下车慢慢寻到三界中学,同学下午已抄小路回家了。怔怔之中,同学的学生一对双胞胎姊妹接待了我们,生火、煮饭、炒菜,娴熟的动作伴着灿灿的笑脸。深秋清冷的夜里,热气慢慢在房间升腾起来。在这寂寥的陌生地域,懂事、纯真的双胞胎姊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记,这也是第一次三界之行唯一给我添上的一抹暖色。
之后,我又多次去过三界,有时听课,有时监考,夏夜,独自一人坐在三界河边,看月光下影影绰绰的村庄、树林以及夜色,山乡夜晚的安宁、静谧不时拨动我年轻的思绪,勾起心底的孤寂,闲愁似河面水气一样排遣开来,罩满了我的全身。
看到同学整天乐呵呵的样子,我很难想象,自己如果长年累月生活在这大山深处,心境会是何种况味?从小在重重叠叠的山峦里长大,渴盼的双眸向往的是山外的世界,是坦荡无限的原野,是湛蓝辽阔的天空。兜过头来,扎进了更深更远的大山腹地,听山风呼啸,看云卷去舒,真不知日子如何熬法!
(二)
但三界一直吸引着我的眼球。最先关注的是它许多富有诗意的村名:青山、水秀、黄金、三宝。多么优雅迷人的字眼,让人脑海里马上浮现一幅幅乡村的画面:小河、石桥、古树、村庄,还有拖着长辫、欲笑还羞的村姑。后来,我陆续去过这些村庄,有的在河边,有的在高地;有的依山傍水,错落有致;有的绿树环绕,古意盎然。后来,我开始留意三界其它村落的名字,学生中有不少来自三界,从他们口中渐渐知道了西湖、翠屏、藕塘、西隅、荆山、林上、大屋场、冷水坪……,它们如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大山深处的褶皱里,闪现着诱人的光芒。后来,我四处询问这些村庄的渊源,想通过搜寻它们历史的点点滴滴,揭开大山严严实实包裹的衣衫,来触摸它们缓慢而有力跳动的脉搏!
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,血管贲张,喧闹有序。幕阜山脉从通山蜿蜒而过,在三界留下了最为独特、最为显著的痕迹。这里山连着山,岭连着岭,山峦层层叠叠,连绵百余里。民谣中“前面大山陡,背后大陡山”,“对面喊得应,见面走半天”,就是这里山高谷深,林多树密的写照。这里是富水河的源头,这里是鄂东南道委机关所在地。
当年的红旗在三界尖上迎风招展,红遍了鄂南的山山水水。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于这里,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儿女长眠于这里。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,湘鄂赣省委特派员吴致民,鄂东南道委书记黄家高,红三师师长谭质夫、政委叶金波,修武崇通县委书记成其福、苏维埃政府主席戴德昌……他们一个个的各字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熠熠闪光,永垂不朽。如今,矗立在冷水坪的革命烈士纪念碑,日幕之下显得孤寂,但青山秀水夜夜与之相伴,也能抚慰这些英年早逝的魂灵吧!
这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,深山藏珠,含而不露。建于清末的郑家大屋就是佐证。鼎盛时期,三界的大部分山林属于郑家,运载竹木的竹排浩浩荡荡直下九江,竹排汉子亢奋而凄昂的号子响彻河岸,叩击姑娘、小伙年轻的心扉。时过境迁,竹排消失了,号子远遁了,余下两岸的芦苇在风中摇曳。改革开放之后,装载竹木、煤炭车辆的嗽叭又揿响了三界的山山坳坳,户户门帘。千百年来,大山总是用自己的血液哺育着平原孱弱的身躯。
郑家大屋座落在三界河边的一处平畴上,门前一口小塘,远处是巍峨的城山。大屋气宇轩昂,仅天井就有48个。相传当年仅筹备石板、石柱等石料就用了整整三年时间。郑家是开明地主,乐善好施,当年的三界河大桥、厦铺河大桥都是他家捐资修建的。郑家还有民族节气,抗战期间,为守住城山要塞、国民党的一个整编师就驻扎其家,与日寇进行殊死搏击。后遭日军报复,大屋被飞机炸成一片废墟。如今,断垣残壁仍在,青石彻成的天井仍在,6米高的大石柱依然完成如初。透过长长的巷道,依稀可见当年大屋的辉煌与魄大。
三界的历史不全是用可歌可泣、可圈可点的笔墨谱写的,也有青山褪色的无奈、双眉紧锁的愁苦时候。我在厦铺工作的那几年,三界虽然韶华不再,呈现出日暮下的颓势,但架子还在,仍然是全县最富裕的乡镇。煤炭、水电、竹木等资源得天独厚,仅林业站就有一百多名职工,他们很滋润地守住两个关卡。三界一条三百来米的土街挤满了餐馆旅社,车马喧腾,人流不息。那时三界的村民是深山的“土豪”,他们卖掉竹木之后,揣着厚厚的腰包直奔县城,住宾馆,吃酒店,惬意地享受着城里人羡慕的眼光。但好景不长,不到20年时间,山林砍光了,煤炭挖空了,大山丰腴的躯体日渐干瘪,健硕的胸脯日渐萎缩,富饶的三界很快成了贫瘠的代名词,河水伴着河床两岸的芦苇一路流淌,一路鸣咽。
这段时间,大山面目疮痍,大山里村民的生活也异常困苦,衣食无虞的人家廖廖无几,多数村民日子捉襟见肘,过得颠三倒四。过去他们有钱无粮,如今钱袋和粮袋都是瘪的。许多生活物品需要购买,购买好了还要肩挑背驭几十里。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是他们不小的一个奢望。没有实地生活经历,真难体会山里人家生活的艰辛与诸多不便啊!
大山里农民吃惯了苦,也不怕吃苦,但有一件事是他们迈不去的坎:送孩子读书。三界地广人稀,几户人家就是一个村庄。有些孩子刚启蒙入学,就要翻山越岭,孩子上一天学,家长耽一天心。那里学校条件普遍不好,加之课外活动极少,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日见消沉,辍学学生中最多的就是偏远山头上的孩子,他们和祖辈一样,难以走出大山的怀抱。
部分大点的村落即便办有学校,也简陋如同缀满补丁的衣裳。这样的学校外来教师扎不下根,他们住下一年半载,抖抖衣衫上的尘土,就杳如黄鹤,一去无踪了。大多数学校的教师只好就地选才,他们大多数初中毕业,一半时间当先生,一半时间干农活,戴上草帽当农夫,放下裤腿上讲台。他们是几代人的启蒙老师,一辈子在山乡僻壤处默默地传播着知识的尊崇。在他们身上,更多显现的是山里人的憨厚与质朴,难以瞥见一丝读书人的书卷气息。
由于粗疏,由于随意,这样的学校时有事故发生。1997年,荆山学校的一名教师,体育课上教学生翻筋斗,一不小心掉入深坑,脖颈上神经被摔断,头部以下部位失去知觉。当时,他刚刚三十出头,岁月从此以后完全褪色。1999年,我随厦铺教育组同志走访看望他时,下半肢已枯如柴棒,令人不忍卒视。妻子离家出走,两个孩子不到十岁,年逾花甲的老母亲眼泪涟涟给他喂饭。多年以后,这一幕时而在我脑海中浮现。十六年过去了,他是否已在故乡的泥土中安息?唉,有谁知道,大山的脊背曾经压有多少这样沉重的包袱呢?
(三)
幸运的是,三界很快缓过气来,1999年乡镇撤并之后,不少村民陆续外迁,三界渐渐沉寂下来,这个内敛而沉稳的汉子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,他用自己强大的肺活量不断吐故纳新,将积郁在胸腔中的郁气浊气清除荡尽,莽莽群山跃入眼帘的又是郁郁葱葱的一片林海了。
这才是我向往的三界,它有汉子一般的沉静、坚毅、忍耐和深邃,它不张扬,也不浅显,风景一眼望不到头,禀性一眼看穿不了。文人墨客怡情山水,因为他们毕生都在寻找灵魂可以放逐的地方,尘世之中,还有什么比灵山秀水更为澄静的呢?山水也钟情文人墨客,因为他们紧锁的心扉只有纯静的心灵、执着的步履、充谥的才气才能开启。谢灵运任职永嘉太守时,走遍了永嘉的山山水水,他将失意与得意融于山水之中,抒写了大量锦绣诗篇,不仅为后世留下了“谢公屐”的美誉,自己也成为了山水诗的鼻祖人物。他是一个通体被山水浸润之人,也是一个能给山水增添色泽之人。
千百年来,山水的肌肤依旧,山水的容颜不变,但人的心绪呢?物欲时代的芸芸众生,真正寄情山水的能有几人?
随着旅游业的日渐回暖,许多地方开始营山造水,往往一处景致、一样景色就招徕了四处游客,他们一拨拨赶着趟儿蜂拥而来,又蜂拥而去。他们把大山变成了闹市,这不知到底是大山的荣幸还是不幸?我常常忐忑,静默大山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和神态审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到来,又目视着他们的离去?
但三界不是这样,三界的名声不够大,三界的路不好走,这里的花不成片,这里的景不成堆。多数游客用孤疑的目光望一望它逶迤的群峰,就掉头走开了。所以,这里清风可以畅意吹拂,明月可以尽情倾泻,还有阳光雨露,可以精心哺育这里的花草树木、鸟兽虫鱼。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城堡,哪里是亭台,哪里是楼阁,梳哪样发鬓,穿哪件衣衫,全是自己的匠心,虽说不上鬼斧神工,但独特的滋味,足以令相知者赏心悦目了。
单纯从旅游的角度来看,三界是通山最后一块处女地和净土,她是待字闺中的少女,寂寞地等待心仪小伙的到来。妆扮好她的容颜,保护她纯洁的肌体不受侵凌,需要我们大家的呵护与溺爱!
曹可俊就是一个对三界有着特殊情结的人,懂得呵护与溺爱。年近花甲的老曹貌不惊人,有着大山一样的纯厚与质朴。1993年,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(现浙江大学)茶学系、有高级农艺师职称的他,丢掉科技局干部的铁饭碗,卖掉县城的一栋住房,携带妻子来三界承包了3万亩荒山,创办九宫山有机茶基地,一干就是20余年。
老曹是个有梦想的人,他的梦想与三界山水的梦想十分契合、交融,他用嫩绿的茶叶为大山的肌体疗伤,一簇簇茶丛挨挨挤挤又列队整齐,它们随着风的号角,沿着山坡一层层缓缓地摇曳,就像一片潮来时涌动着的绿色海洋。
老曹用20多年的时间,为三界增添了另一道风景!
(四)
三界浩浩淼淼的林海中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太阳山和太阳溪了。这一高一低镶嵌着的两颗明珠,折射出三界耀眼的光芒。
我第一次听到太阳山和太阳溪时,心里就有一股莫名的悸动,多么美妙的名字,阳光般清澈、纯静而夺目,既有金属的质感,又有秋水伊人的唯美。他们相依相偎,是一对永恒的恋人,生死与共,世世缠绵。
太阳溪是三界河里丰满诱人的一段,这里沟壑纵横,处处是幽深的河谷。河岸两边长满了枫杨与杂木,将河床遮蔽得严严密密。大部分时间,河水浅浅地流着,悄无声息,经过滩头时溅起无数晶莹的水珠,滚落深潭。深潭里的水色仿佛突然洇染了一般,全是高山或高原上湖泊特有的那种绿,绿得叫人心悸。河床里没有水草,看不见鱼虾,轻轻掬起一捧河水,让它从指缝中慢慢溢出,那种澄明,那种纯静,似乎澄明纯净得如同婴儿的双眸,没有一丝杂色。倦了累了,坐在河边的鹅卵石上,眯着双眼,嗅着河面上隐隐而来的水气,那真是醒目养神的惬意事啊。
夏季,沿河溯流而上,脚下,是凉沁沁的河水,眼前,是簇拥着无数生命的绿色青山。山水脉脉,物我交融,还有什么烦忧与愁肠不能洗涤呢?与其说是一次濯足,倒不如说是来这里濯心啊!
从太阳溪抬头东望,便是伟岸、挺拔的太阳山,太阳每天从太阳山上升起,普照着山上的树叶、花朵、泉流、瀑布,它们在风中抖动,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芒。这里处处涌动着旺盛的生命力,高大的,矮小的;幽香的,苦涩的;鲜艳的,枯萎的,上苍将它们一层层地攒在一起,一下一下地跳动着大山的情怀。
太阳山又像个婀娜的女子,站立云端,人们看得见她曼妙的身姿,但难得一睹她圣洁的胴体。她不像大幕山上的杜鹃花,一眼望去,赤裸裸地开满山头,烈烈扬扬地绽放,燃烧了山山坡坡,也燃烧了游人的眼眸。太阳山妆裹着层层衣袂,她是温吞的开水,不滚不烫,看不到升腾的热气,移唇品咂,却有一股甜浸浸的温熨滋味。
太阳山让人慕名了许久,也梦寐了许多,但多数人浅尝辄止,登不上它傲岸的双肩。它不像九宫山、大幕山,风景就在大道的尽头,春色已被人间阅尽。它没有通衢大道,只是崎岖小径,层层叠叠的山峰,蕴含着叠叠层层的风景,秀色三分,餐饮者能有几人?似乎只有一位古人独领了风骚。
他就是刘伯温,大明朝开国功臣之一。深山藏古刹,古刹藏高人,似乎也是中国独特的山水文化。在太阳山山腰开阔的腹地上,座落着安平寺,庙宇不大,上下两重,一百来个平方,但这里却是刘伯温的终老之所。刘伯温是福建青田人,辅朱元璋鼎定天下后功成身退,在朱明王朝,刘伯温这样的退隐之人,自然不会选择名山大刹,也不会选择叶落归根,但满腹的天文地理与锦绣才华需要灵山秀水相应和。他从京城一路踽踽而行,走过了千山万水,在哪里止住脚步,他一定数度犹豫过,徘徊过,但最终将步履留在了太阳山上。从此,他的胸中放下了经国安邦的谋略,装满了太阳山的万千丘壑。
刘伯温早已老去,太阳山还像太阳一样年轻。太阳山会不会像刘伯温一样在缄默中慢慢老去?我希望是又希望不是,说不清的情感,道不出的滋味。听说,太阳山的开发已在酝酿之中,未来的三界,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脸孔呢?
我只是希望,三界这方水土,永远是灵魂可以安歇的地方。
上一篇:回 家
下一篇:红十字师资撬车门,争分夺秒救伤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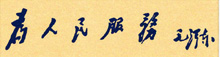




 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
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 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
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