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初,回故乡,拜年。
汽车从106国道通山寨头站减速,驶向通往文宣的乡村公路。正担心那坑洼不平的道路是否泥泞满地,抬眼,却见道路已拓宽刷黑,能两辆车并排行驶,不用提前在弯道处让车。车行其上,一路坦途,无比惬意。水田里,稻茬横竖成行,白色的家豚在低头觅食,麻灰的鸭子扇起双翅从一个小水凼飞赴另一个小水凼,“嘎嘎”叫唤,声音劲爽高亢。
田野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,亦是温煦的,我鼻翼扩张:久违的故乡气息。
大哥在祖屋宅基上新建的楼房贴着红对联,门前一地的红爆竹灰。暖阳中,小辈递烟送茶,笑语盈盈。乡情在相互关切中,复位往昔的记忆。
我将喧闹抛之脑后,照例去看看父母生前的菜园。
白菜、芥菜、萝卜菜,青悠悠,装点寂寥的山洼。那个弯腰掐菜薹的苍老背影是母亲吧?那个荷锄而归的老人莫非是老父亲?眨眨眼,眼前依然只是一片青葱。视线却望向山的那一边,我的至亲在山那头已安睡了多年。不知轰轰烈烈的喜庆鞭炮声与我深沉的脚步是否惊醒了慈爱的双亲?腊肉香,糍粑甜,包坨圆,团团圆圆。游子归矣,亲在何方?
回头,猛然发现老屋门前禾场边的大柏树没了青绿!
这棵古柏高8丈,树围2.2米,冠盖面积达20平方米,是文宣村最为高大粗壮的护村树。家谱记载,乃我高祖父成德霖公亲手所植。树上钉有铝牌:国家三级古树,树龄150年,通山县人民政府二00七年四月。屈指算来,树龄有164年了。细看,树身密布小孔,是可恶的虫子噬害了这棵树?还是久旱干涸枯竭了他的根系?不,幼年时我看到的这棵高耸云天的大树就爬满了虫蚁,100多年来,无数次大旱之年他却毫发无损,风吹不倒,雪压不垮,一年又一年,茂盛的枝条不断往四周拓展,凌霜傲雪,直指苍穹。
这是棵神树嘞!
那年,同住一栋老屋的宝善叔公见树枝粗壮枝桠下垂,来往行人若是扛树或挑长茅柴必被枝桠挂住,出行甚是不便。一个午后,他将柴刀插向腰背的刀箧,“噗噗”往两个掌心吐点口水,三下两下爬上了树叉,挥刀往枝条砍去,手起刀落,“哐当”一声,刀掉在地面。宝善叔公溜下树拾起,继续砍,刀子尚没挨着树枝,头朝下脚朝上,一头栽了下来,跌个鼻青脸肿。众人大惊,问他,一生砍的柴能用火车皮装的他一脸懵,结结巴巴:有人按着我的后脑壳将我往下推。
之后,任由树枝干枯,自然掉落,再也没有人敢上树砍枝了。
幼年时,我们女孩子在树荫下跳绳、打石子、跳房(画成房子形状,丢石子单腿拐占地盘);男孩在树下玩扑克、两膝对拱、爬上树掏鸟蛋;逢年过节时,各家各户将稀缺物端到树下,祭天祭地请祖人。老人们在柏树下抽着自制的卷烟,谈古论今,唾沫飞溅。人与树,和谐相融。
古树守着老屋。
老屋为砖木结构,一连五间,一进两重,中间是三个天井,两侧为厢楼,左右各建有披厦,乃我曾祖父三兄弟所建。曾祖父弟兄断文识字,送子求学,是以,我祖父这一代都是读书人。20世纪20年代,军阀混战各自为政,民不聊生。我祖父与他的兄弟、堂兄弟穿着长衫从老屋走出,告别高堂与柏树,踏上了救国的道路,此后,皆先后壮烈牺牲,留下“一门八烈士”的英名。其中一个南征北战多年,与老家失联,写信回乡时特地注明:我家门前有棵大柏树。
老柏树目送他们远行,一定也为他们血战疆场默然垂泪。
“门前古柏绿荫浓,叶茂枝繁耸太空。冰雪千层生傲骨,狂风猛袭仍从容”。堂伯成华之面对虬龙般的古树,吟出了我们的心声。
随着我父母相继仙逝,此后,老屋无人看管,日渐坍塌。当最后一根大梁从高耸的房檐坠入泥土的暴雨之夜,百里之外的我在梦中仿佛听到了老柏树的怒吼,第二天一大早打电话给老家的大哥,哥说,你是心灵感应,老屋垮了!
古树见证了植树者从一个人变成七代人的全过程,他还可以见证子孙无限地延续,他欣慰一个家族的昌荣。
然而,他干枯了!
他不是老而枯的。
2018年,当古树旁全村人赖以生存的阔大山泉井被改建成深井,大理石辅以水泥与沙石,牢牢地铸筑在四周,曾经一脉清泉川流不息,如今再也不能绕着山边叮当外流,老柏树的根系无法汲取地下泉的滋润。雪上加霜的是,邻家建房时,图省事,将山边挖掘的土填在柏树四周,造成土层上升,将树身埋了一丈多高,水量赶不上消耗量,长时间缺水,郁郁而枯。
家人说这柏树枯了三年,却屹而不倒。我抚摸他干裂的树身,黝黑粗糙的树皮一道道如山涧丘壑,那是岁月的年轮,镶嵌着一个村庄一个家族的记忆。如今,父母没了,老屋夷为平地后重建,已不复昔日的影子,每年春节,能让我回故乡的唯一记念就是这棵柏树。如祖如父的柏树啊,愿您如大漠中的胡杨,千年不倒,兀自伫立,兀自铮铮,兀自不朽。如此,有生之年,我还能在岁末年关时,奔向您,奔向故乡的怀抱。(作者:湖北省咸宁市女作家协会)
下一篇:风起缘来恰逢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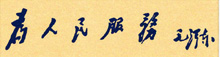




 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
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 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
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