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 张长征
山坡上的桔子黄了,隐水村的土地上又生出一股酸甜的味道,郑家的屋檐下挂满了一墙子的玉米结,黑白的老房子又冒腾出一抺袅袅炊烟。郑安国笔下的《简朴乡愁》出来了,拜读已久,常掩卷又复读,几许漂泊思乡的情结浸漫了我的全身,那种酸甜的乡愁,在缱绻的时光里漫延开来。
认识安国是在十几年前,我从深圳的创业中落魄后,龟缩在通山小城,常与几个文友在他的酒馆里聚酒,他留着小平头,根根头发硬生生笔挺地竖着,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简单的休闲式,一条牛仔裤,上身总是搭配一律的黑色,其它色系就鲜少见了,给人一种成熟、英俊与爽朗。
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开着偌大的餐馆,盘算着每天的迎来送往,处处是道,条条有理,他迈开八字步就有一股旋风般的速度与激情。几杯酒下肚,往往无话不谈,我喜欢飘浮起来不生不死的麻醉感。酒逢知己千杯少,无忌惮地说酒话,任性情自流。而他那在酒场上那种不紧不慢,慢条斯理的样子让我常数落,安国三面敬杯,哥啊姐啊叫个不停,让人听着酥软而尽兴一饮。酒,他喜欢是大口的焖,饭,他爱用大碗的盛,均有过人之量。
安国先前在南方某大媒体打拼多年,算是文字界见多识广的媒体人。文人聚会时,好谈某某散文写得好,某某古体诗很不错,某某小说有意味。但他遇此话题从不作评论,默不作声。通山那年,陈荣辉老兄英年早逝,安国写了一篇《他,撒泡尿去了》。呃,在这篇新诗中,初识他那淋漓尽致表露出痛惜、悲苦、怀念之情,其字里行间带着一股愁苦幽怨的文风,这是我喜欢的。后来,他和几个文友整理逝者的小说文稿,免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其结集出版,让逝者欣慰瞑目。呃,这个人,文如其人,亦商亦文亦是情中人,有大爱、有情义,值得一交。
时光,常会在生活的拐角处转弯,又在转弯的拐角处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过往。那年,餐馆业随波浪般退去,安国束手无策,在残茶剩饭的日子里,他低沉而茫然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父亲又查出了带晚期的癌症,更糟糕的是正处在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,在医院过道里却奢求不到一张床位。在封闭期间,他用孝心与真诚打通了层层关卡,不间断地从咸宁往隐水为父亲送药。年过六旬的父亲还是走了。沉重的打击足足让他两年没有回过神来。此后的日子,他在为生活拼搏之余,三不五时回到乡下,探望母亲,走上熟悉的故园,打理着父亲留下的四十亩果园。扳算着二十四节气,他像父亲一样勤扒苦耕,守望着春播秋收,他又以双手托举起妻子、儿女,在生硬的城市里,撒开两腿奔波于生计,在晨暮星光中,以孤独与痛楚去抒写了大量的文字。安国是一个文弱书生,又是一个铁打的汉子,介于此种双重的生活模式,《简朴的乡愁》应运而生,自然而然,寻常又不寻常。
没有生活的疼痛,写不出《简朴的乡愁》的真。
写散文贵在于一个“真”字。真实,真话而真情方能打动人,让人越读下去越爱不释手方为佳作,做作、虚无和缥缈的作品终难以上乘,读着读着让人厌恶起来,剩下的根本无法读下去。读安国的《简朴乡愁》却不一样,晨翻夜读而不生累。写人、写景、写物、写情,均是作者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,在一篇又一篇的构思中,运用灵巧的文字与精巧手法去娓娓道来,以自己的亲身疼痛经历去感悟人,去打动人、去鼓舞人,带着读者融会在文字之中,引起共鸣,带来边阅读边联想的愉悦之感,我认为这是好作品。
人物,站在乡愁里始终是主角;景物,往往应是情感的宠物。安国的作品中写个体人物极少见,但少而精巧,却在景物运用和个人情感所花的描写笔墨居多。
我喜欢安国写人的技巧,开篇中写偶然间看见一个陌生的美丽村妇,先用视觉镜头推出其人身体动作、装束打扮、形态神情,以及自作多情的铺垫,却没有任何对话。自问“这是谁家媳妇?”,自赞:“结实、健康、纯朴”,自答:“像我的表嫂!”,从陌生的村妇到熟悉的表嫂,从村妇的“美”到表嫂的“真”。这样的伏笔一经揭开就让人怦然心动,瞬间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,人物形象突兀地豁然跃入了脑海。
语言生动就是人物鲜活的证明。比如,在《回不去的故乡》一文中,二十二岁那年,儿子扛着沉重掩鼻的粪桶,牛一样喘息着踉跄前行,父亲黑着脸在背后气咻咻数落儿子的愚笨,并大发感慨:“将来弄得不文不武,只怕讨米没人给”。儿子又累又气,当在半路上突然接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时,一时半是凄惶一时半是欣喜,他立即扔了粪桶,而父亲依然黑着脸,没有一句表示高兴的话,只说一句:“崽,你命好”,将粪桶扛起匆匆而去。短短的前后语言对比,简单的场景描写,将父亲的对现实农耕生活的屈就和儿子对将来生活的不甘心,以戏剧性的演绎、以疼痛感的艺术呈现出来,正因为有了生活中那种哀毁骨立的伤痛,才能抒怀出生动的朴实与纯真。
没有生活的悲怜,道不出《简朴乡愁》的善。
我也是从农村苦水里趟过来的,童年的生活就是泥巴的样子,如泥巴的房子、泥巴的小路、泥巴的土地、泥巴的井口、泥巴的灶台、泥巴的童趣。离开家乡这些年,农村大变迁不再是从前的模样,后生的一代一代人嗅不到那种泥巴里的贫困生活,那年代泥腿人的苦涩记忆就成了乡愁。安国不同,这些年往返于城堡与乡村之间,其实,他一直没有脱离过土地的演变与滋润,更重要是,他一路伴随泥巴走来,并不断地在乡愁里调和色彩,所以,简朴的乡愁里充盈着乡里人在前后大变化中仍保存着固有的善良、简单与纯朴,这些恰恰是对乡愁的经典表白,也是怀旧的本质属性。
写散文者,可见风花雪月的事居多,儿女情长的也不在少数,好多散文先写着写着还算顺溜,到后面往往脱轨了,偏离了作者内心里的感情,生有无病呻吟之感,即就是形是散得好,而神与魂不知去了哪里。而安国的《简朴乡村》把握住了形神结合的上下刻度,大部分的篇章高度虽不一,但又有其独到之处,读者可以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在《与一场大风相遇中》里,“面对这场大风,…恐慌…摆脱、逃离…蹲下…藏下来….唯恐被风席卷而去….实际上,来势凶猛的风或许并不认真看我,像选择一条便道似的,从我的眼皮底下穿过,而根本不会把我抓住,在他的眼里,我大概还抵不上那株不声不响的高粱。”个人的遭遇与物件的际遇遇见时,他进行了心神领会的融合,苦涩、懦弱与渺小,有时在生活中还真的是弱不禁风,但不经风雨又怎能又有高粱熟了!借用一场风与个人的情感触碰,灵感派生出另一种希望物种的寄托。这种暗喻的构建是散文的亮点之处,让人心智随之一亮,作者在《简朴乡愁》中写风的文章有好几篇,但手法大都运用了以借景抒情的态度,一一读来均耐人寻味。
《挽歌》是一篇为写从猪的生养到屠杀的命运过程,终极的哀嚎称为挽歌,万物皆有的灵性与宿命,他以人性的善良、灵魂、苦涩、悲怆对生命进行一一拷问,对每一个最后发出嚎叫的挽歌,产生了对各种生灵的声音思考,那是生命是多么崇高,是那么的绝望,又是那么的依恋。安国从筑猪圈、养猪、杀猪过程说过来,最后,他所联想到了村庄的现存老人有养猪之气力再无杀猪之力气,年弱的侍弄几只芦花鸡、梅头鸭,打发生命的剩余时光,一旦刀挨上脖子,挣扎着唱几声挽歌,但都不够嘹亮,不足以叫醒一个村庄的耳朵,折射出乡村年轻人往外走的窘迫与不甘,老弱者对留守乡村的无奈与困顿。他写道:“哪怕一棵树一棵草,在面对一把锯子、一把锄头的时候,它们分明也在尖声地嚎叫”。他又在文中写道:“这世间所有的生灵,在面对生命的流逝时,都和人一样,充满了彻骨的悲凉”。想一想,人世间,多么无情而美好,生命里,多么顽强而脆弱,何况善良的人们呢?
没有生活的感悟,说不出《简朴乡愁》的美。
人活一辈子,想让你做的完美事情太多了,有的人一辈子一直在纠缠不清仍要去牵肠挂肚,越执着就越悲观,短暂的生命终结了,矛盾仍然在纠结,还在延续与传承,特别是惟利是图、贪得无厌的人,视人生成功与享受为至高目标的贪婪者,致使在人世过程中上真正属于应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,却被弄没了,或自己弄脏了,临死也没有醒过来。散文家周国平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有悲观垫底的执著,实际上是一种超脱”。
读郑安国的散文,对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有所感悟的东西很多很多,向往美好、热爱美好好多东西其实就在身边,散文的真正的魅力就是展现生命的真谛。郑安国在乡愁情结中,以一风一物,一草一木的感悟为真正的生活去解密,他生活里发现生活,真实与想象的距离并不遥远,原本就存在于一个个光亮的、不被人注目的细节之中。这个细节就是顺应平凡的生活。
乡愁,自古以来的诗歌也好,文章也罢,百姓珍藏的佳句妙篇也不少,一揽子下来,喜欢写乡愁的墨客多的是,其实,乡关何处是,处处是乡愁。乡愁,其情感本质“身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之痛感,又困于心境不一,所能表现的却大同小异,写法上也异曲同工,一个人若对所处客地的陌生环境,就定有对之前熟悉的环境怀念与感悟,每一个人所处的家乡环境不是一样的,何况乡风、乡俗,境况、环境均不同一色,所以,时过境迁,背景不一,写出来的东西也肯定不一样,江南水乡与大漠边关不一样的,大漠人肯定悟不出江南的楠竹隽秀,江南人肯定写不出大漠的孤雁哀鸣。这恰恰又是语言文学所能融会贯通于南北的魅力所在,搭建了互能欣赏对方的不同之美。
安国的简朴乡愁来自江南水乡,不可能把握住塞北的乡关悲烈,他所能表现的是江南儿女的温润柔情。所以,他展现了江南之美。他又是江南的隐水人,题材始终带着本土的底片。
在《竹子的历程》里托物言志,表达了对村庄美好的愿景,以《风车》的象征意义,表达了时代进步中的可喜变化。在《月光》、《又见荷风》里,他运用对比烘托手法,寓情与物、即景抒情,体现了作者单纯的随意而发,随地而行,随言而散,表述短暂,联想爆燃,但表达中心的思想与情感的主旨能又明确而集中,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把握得相当的准确而得体,这种表现方式与手法让人让各段乡愁的影像在严密衔接,阅读起来生出舒服感。再就是其行文中的运用了以小见大、以大见小的表现手法,如《蚂蚁》、《与蜗牛相遇的时刻》是以小见到大的表现手法,如《东坡如水》、《西湖情思》又以大见小,在交错的、复杂的、交融的写作方法上,安国何尝不是在尝试着运用用一种以“不惜千字散出去,唯将神情请回来”的意景,在努力寻找出体现出人们精神里所追求的共同真善美,那即是时代之需求。
安国的乡愁在最后篇章中有读者的共鸣之处,那就是寻找乡愁去了哪里,乡愁,并不是他的专属,乡愁,而是大众的归属。他去过我的故乡,在《湖山语境》里寻问过我乡愁,他去过远方朋友江明大哥的宽窄巷,求解何处是乡愁,在书香芃芃中、在雨山半日、他呆立于西湖情思里,守候着白马寺的黄昏,乡愁,真是“郑家戏班乡风记,一味乡愁度盛夏,陌上稻香江南远,时光静止千千结”。
坊间传言,郑安国出版了26万字的集子不足为厅,这本书只是他文字里的冰山一角,才人若窘迫于生活,出书更是十分不易的事,他正厚积薄发,他一定在等待暴风骤雨的到来,洪流将倾泻而出,我在期待。
上一篇:铁塔共享单车为嘉鱼马拉松助力!
下一篇:冬登望陈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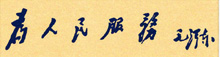




 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
通山大畈祝家楼村跻身 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
宜黄县梨溪镇:人大代表